到底流入多少白银?保守估计,当时世界两到四成的白银都流入中国。 关于明清之际白银的数据,各类研究很多,不少学者目标都是给出自己的标杆,在这一领域留下参照系,不过我在《白银帝国》探索志不在此,不仅希望提供不同视角提供给读者参考,而且更期待通过梳理分析破碎史实以呈现更为核心连贯的货币逻辑。白银不同数据异同之外,应该看到更大的格局,即在数据之外的逻辑衍生与历史脉络。
古代经济估算不容易,即使安格斯·麦迪逊(Angus Maddison)之类经济史巨擘,其对世界GDP的估算成为最权威来源之余,其估算本身也存在诸多争议。具体到中国白银,不仅涉及各种度量衡,而且资料来源零散而单一,因此读者应相对冷静对待各类白银流入与流出数据,在数字之外更留意趋势的变化。
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·S·兰德斯(David S.Landes)所言,在推测性的计算中,数字只有与历史背景相符时,才是可信的 ——毕竟在长时段的计算中,任何参数的极小误差最终都导致结果的极大偏移。我一直认为,理想的经济学,是数据、逻辑与历史的结合,而理想的经济史研究,则应该在理解数据的背景之下始终抱有疑问。
白银流入到底为中国带来了什么?这也是英国纪录片制片人Susanna Thornton(宋愫愫)来上海和我主要讨论问题。
首先,白银与市场的结合对抗了皇权意识,白银的流入,不仅使得元之后历朝帝王屡次禁银的努力付之东流,也使得中国经济加速货币化,无意间进入上一次全球化搅拌之中。对比之下,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也为欧洲增加了动力,开始了工业革命,主要经济体在清代之后陆续进入金本位乃至纸币时代。只有东方帝国,仍旧静静地固守着白银,最多不过纠结下白银流出或者流入不足。
其次,政治之外,经济也受到海外白银的搅动。白银流入增加时,中国经济的货币化提速,我们见证了《金瓶梅》中的人人皆商以及清代江南地区的富庶景观;当白银流入减少,中国饱受紧缩之苦,甚至引发了战乱与起义,无论在明末还是清末皆是如此。繁荣时刻的白银是锦上添花,衰败时代的白银则是最后一根稻草。
最后,货币只是历史的一环。正如货币金融学大家弗雷德里克·S·米什金(Frederic S.Mishkin)所言,金融系统是经济的神经。而生生不息流动的白银,则是中国经济的白色血液,其动静变化,牵动中国经济神经,造成一次次兴奋与痉挛乃至紊乱。
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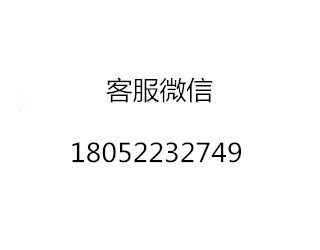
 精彩导读
精彩导读






 热门资讯
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
关注我们
